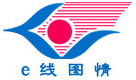别具一格的历史画卷——评《雍正十年:那条瑞典船的故事》
2011/2/12 点击数:367
[作者] 刘文瑞
[单位] 刘文瑞的博客
[摘要] 一本具有自己的鲜明风格、截然不同于其他史学专著的书籍《雍正十年:那条瑞典船的故事》(阿海著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),通过对1732年第一次来华贸易的瑞典船弗雷德里克号相关史实的描述,娓娓道来,给我们展开了一幅绚丽的历史画卷。
一本具有自己的鲜明风格、截然不同于其他史学专著的书籍《雍正十年:那条瑞典船的故事》(阿海著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),通过对1732年第一次来华贸易的瑞典船弗雷德里克号相关史实的描述,娓娓道来,给我们展开了一幅绚丽的历史画卷。
《雍正十年》是一本可读性极强,而且富有创意的史学著作。由于它采用了“讲故事”的手法,使历史人物和事件以文学笔法再现出来,在这本书中,我们可以看到趾高气扬的来华贸易大班,算盘打得贼精的广东海关官员,承担对外中介使命的行商,在官府和洋人之间两头受气的通译,荞麦皮也能榨出油来的海部大人下属家人,狐假虎威、不放过任何勒索机会的衙役,各色人等粉墨登场,演出了一幕活灵活现的历史剧。这本书读起来完全没有常见史书的那种枯燥乏味,但它又完全不同于时下流行的“戏说”式描述,而是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可靠翔实、言之有据的远洋贸易中的生活场景。对这本书,可以借用一个人们熟悉的准则——“信、雅、达”来形容。尽管“信、雅、达”是公认的翻译标准,但用来要求原创作品也未尝不可。
所谓信,是指这本书的资料可靠。作者所依据的基本史料,是来自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,尤其是以弗雷德里克号远洋船大班坎贝尔的日记为主,辅之以卡尔王子号的船上日记、贝尔基金会收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爱尔温档案、芬兰号随船牧师瓦伦博格的原始记录、瑞典航海史博物馆收藏的东印度公司后甲板大副霍尔姆的手稿,除外国的相关资料外,作者还参考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,充分利用了国内的资料汇编。可以说,几乎能够见到的相关资料、重要专著和代表性论文,都进入了作者的视野。正如作者所言,这本书所提到的人物和事件,都来自于历史档案,属于严格的信史。凡是有过写作经历的人都知道,对于用不同文字形成的档案资料,特别是涉及到人名、商行字号等名称,要恢复外文音译中的原始真实汉文,任务是何等艰巨!尤其是在汉文档案中寻找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行商,难度不下于大海捞针。而这本书的作者基本上做到了,除如升行的行商Mandarin Quiqua一个人外,其他都查证到了真实汉文姓名和字号。这种在史料堆里仔细查证的“水磨功夫”,在当今学界已经罕见。张中行先生称这本书“翻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,记载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真实信史”,恰如其分。
所谓雅,是指这本书富有文学色彩。中国史学界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文史不分家,从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起,史学就与文学处于零距离状态。好的史书,肯定富有文采。《史记》中的本纪和列传,无一不浸透着文学气息。使人读来琅琅上口,描写事件则如临其境,描写人物则如闻其声。尤其是其中的鸿门宴、细柳营等等,脍炙人口,既是文学史上的经典,又是史学史上的经典。可惜的是,随着时代的转换,这种优秀传统当今已经式微,现今的史学著作,当然有写的好的,但离文史不分家尚有差距,有些更是语句晦涩,文法死板,大有把读者吓倒的架式。可喜的是,《雍正十年》在一定程度上努力恢复文史一家的传统,试图给读者讲出一个细节可靠、语言生动的中外交往故事。从该书的整个叙述来看,这一努力收到了成效。全书的文字平实,注重细节,而平实中不乏生动,细节中展现文采。通读全书,不仅能了解到这条瑞典船的贸易史实,而且能够感受到瑞典大班坎贝尔的精明狡诈,海关监督祖秉圭的老奸巨猾,抚院海部杨文乾的干练和刚愎,行商陈寿观的阿谀奉承,行商陈芳观的犟驴脾气等等。雍正时期的社会百态、人物心理、风俗习惯、中外差异,一一展现于读者面前。
所谓达,是指这本书说理透彻深邃。作为历史著作,如果只能告诉人们陈年老账,无法体现历史背后的智慧和启迪,就不算上乘的作品。《雍正十年》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,而是在故事中包含智慧,在情节中表述道理。通过书中的描述,读者可以看出,早期的中外贸易是如何孕育出了中西文化冲突,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差异何在,新航路开辟后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等等。书中的故事,足以纠正人们原来在中西贸易方面的某些认识偏差。比如,行商地位的形成和演变,中国官场规则和西方贸易要求之间势不可免的对抗等,显然有其由来。某些细节,还可以补充正规史书的空白和缺失。例如关于船只丈量和征税的细节,外国大班同中国海关交往的细节,洋货采买和交易的细节等等,可以使读者得到充实可靠的知识,进而从中体味历史的沉重和深邃。尤其是对粤海关三任监督杨文乾、祖秉圭、郑伍赛的描述,几乎把中国官场的各种明暗伎俩和显潜规则都揭示得淋漓尽致。
当然,任何图书,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,《雍正十年》也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。从整体上看,该书的讲故事形式是可取的,但作为史学著作,场景的纵深似乎不够,在当时欧洲与东方贸易的整体观察上略显薄弱。另外,作为文学色彩浓厚的著作,故事的剪裁和叙述还可以有更精当地展示。个别地方尚有一些错失。例如“趋之若鹜”的“鹜”,写成了“骛”。“鹜”本来指野鸭,转眼变成了“骛”即奔驰的骏马。人们有一种心理,越是好的东西,越是近乎苛求。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批评,是为了将来看到该书作者更好的作品。
中山商报 2006年3月31日 第 296 期 A14版。
原文连接:http://wenruiliu.blog.163.com/blog/static/24285622201111211568610/